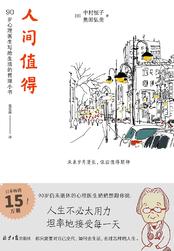随梦文学>梦春日暖 > 第50章 心动 裴吉哥哥不让那裴台熠哥(第2页)
第50章 心动 裴吉哥哥不让那裴台熠哥(第2页)
“你我的婚事,已经办完了。”裴台熠语气平静,似是在告知她。
“哦。”宁窈意外但又没多意外。意外是她都不在,婚事是怎麽办的?不意外是,她不在还办婚事,非常符合裴台熠的脾性。
裴台熠用手掌擦掉她脸上残留的眼泪,继续道:“你现在,是我的妻。”
话中深意,不言而喻。
八擡大轿,明媒正娶。
她彻底属于他,她的呼吸,她的笑颜,她的身亻本,他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她予取予求。
同样的,他也完完全全是她的所有物。
宁窈的心在胸腔里从左边撞到了右边,那剧烈的心跳,叫她快喘不上气。
成婚前,女子的陪嫁里,避火图必不可少。
她又是医女,更是清楚夫妻是何事。
但知道归知道,眼下裴台熠真要将那东西放进来,她还是紧张得浑身僵硬,动弹不得。
她偷偷看过许多闲书,那书里总会描绘新婚之夜女子的疼痛,而女子越痛,哭喊得越惨烈,男子从中就能得到更多的乐趣,仿佛女人注定要挨一刀劈才能算完整。
她好怕痛,于是一想到这些,便应激似的死死抓着身下床褥。
那双灵鹿般的眼眸,蒙着一层水雾,可怜兮兮地望着他,眼里布满惊恐和畏惧。少女太纯美,那不通人事的青涩,与对他显而易见的依恋汇聚交织在一起,便编成了邀请的味道。
裴台熠目不转睛地,盯着宁窈的脸。
他不放过她面上闪过的任何神情。
颤抖的睫,拧在一起的漆黑的眉,低低吐着气的樱花色的唇。
被褥下,裴台熠大手一路往下滑。
手指上粗粝的茧,像锋利的刀刃,一寸一寸刮开了她的皮肉。
他突然握上她的脚踝,将她猛地往下一拖。
就在宁窈惊恐万分地紧闭上双眼,那预想中刀劈斧凿的疼痛却悬而未落。
取而代之,是裴台熠将她伤痕累累的小腿,搁在了自己的膝上。
他从床头取来了金疮药,冰凉的药膏被掌心熨热,然後缓缓在她小腿上推开。
腿上深深浅浅的伤,有的结了痂,有的还没有,往外冒着血珠。
宁窈方才神志没放在伤口上,便不觉得哪里疼,此时裴台熠为她涂药,她才疼得直皱眉。
裴台熠手掌粗,但涂药时却力气轻,那只手从她的脚踝往上挪,在细密的疼痛之外,又让宁窈有另一种感觉,不由咬了咬嘴唇。
待涂好了药,裴台熠又将她的腿放回被褥下,掩了被角,起身去屏风後的洗手池里净手。
宁窈出神地望着裴台熠倒映在屏风上的背影。
她听说,男人一遇到那方面的事,就会变得既无道德又无良心,与野兽无异。裴台熠为她解毒时没碰她,是因为他们当时还没成婚。如今他们已经是名正言顺的夫妻。做丈夫的,不会不想享受自己的权力。可裴台熠看起来,似乎并没有那样的打算。
“你……”宁窈很小声地开口。要她问得直白,她真做不到,嘴唇嚅嗫,挤出一个含糊不清的音节——“你不,不……做吗?”
她说话的声音很小,前半段裴台熠其实并没有听清楚。他只捕捉到了最後一个字,“做”。他沉了沉脸色,大步朝她迈了过去,钳着她下巴,叫她擡起头,然後俯身就是一通泄愤的吻。直吻得宁窈眼角泛红,面如桃花。
“你腿都这样我还x你,我是秦兽?”
宁窈到底是从小养在深闺的小姐,哪里听这种粗鄙之语。裴台熠也是从小在皇宫养大的天潢贵胄,平日再脾气不好,也不会吐出这般粗俗言语。所以当他贴着她的耳朵,说出“x她”这种话。宁窈先是小脸一白,紧接着便满脸通红,甚至连脖颈都是红的。
“你,你……”她又羞又愤,羞是羞这词辱没了她的耳朵;愤是愤裴台熠这人这般坏,真是看错了他。她气呼呼地擡脚就踢在裴台熠小腿上。
裴台熠反手将宁窈的腿按了下去,然後缓缓分开,又俯身去亲她的淡粉色的膝盖。“急个什麽劲儿,以後我都是你的。”他抱着她,嘴唇贴着她的耳朵,发出一声促狭的笑,他拍了拍她的背,温声细语。
宁窈对裴台熠这种倒打一耙的行径不可思议,“你,你,我,我才没有急!”她嘴上说没急,但却急得满脸通红。她急裴台熠觉得她急!
宁窈越着急,裴台熠越觉得好玩。他抱着她,又滚到火红的帐子里去,“不做也能舒服会儿。”
他先用了手,然後是吻,按照方才一点点从她身上摩挲出来的地图指挥作战。等宁窈汗涔涔地从帐子里爬出来时,已累得连手都擡不起来。她像猫一样趴在裴台熠胸口,双眼没有焦点。
“好点了吗?”裴台熠单手搂着她,轻轻拍了拍她的背。
宁窈泪眼汪汪地去看裴台熠,裴台熠没有她这般狼狈不堪。除了头发乱了些,衣领乱了些,呼吸乱了些。他还是和平常时候一般,甚至连身上的衣服都穿得好好的,黑玛瑙纽扣一直系到了最顶端。
宁窈觉得自己有一种,又落下风的感觉。
不能这样,不能总是她在裴台熠面前出丑难堪。
她想让裴台熠也变得像自己现在这样。
失控,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。
她死性不改地,又悄悄将小手一点点挪到了他腿上。
裴台熠的反应非常大。